资讯分类
陈思诚 电影世界中最精明的产品经理 -
来源:爱看影院iktv8人气:953更新:2025-09-10 20:3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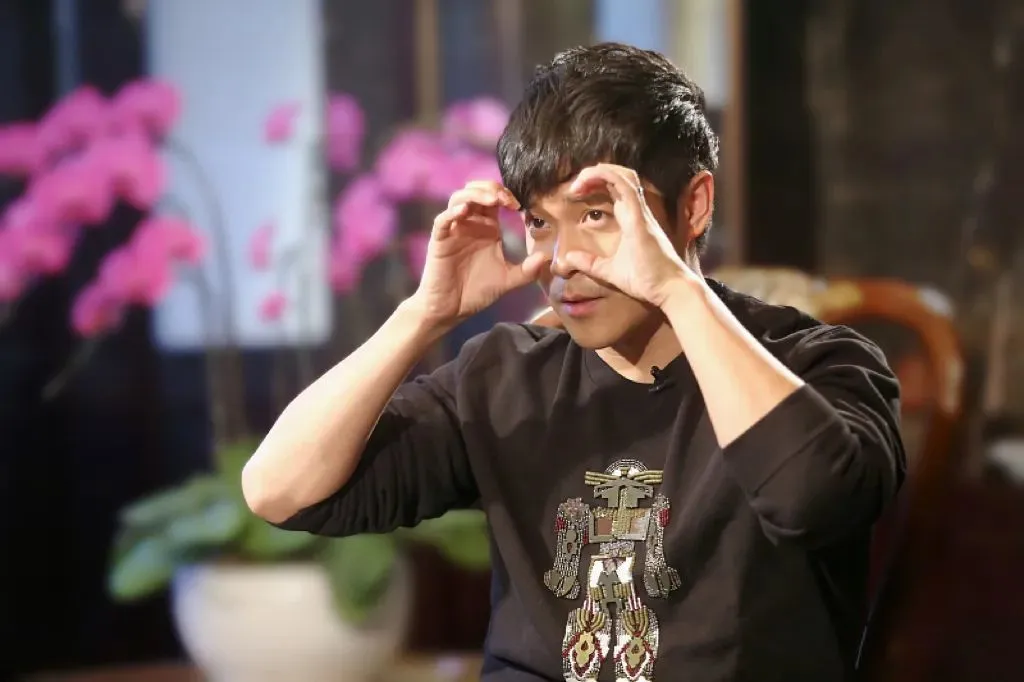
截至7月15日中午,电影《消失的她》累计票房突破33亿元大关,有观众评价称这亦是「陈思诚式创作」的一次显著成功。所谓「陈思诚式电影」,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市场下沉策略的具象化呈现。在当下中国影视产业中,这种下沉已演变为一种系统性现象:媒体领域从编辑主导的精英审美转向算法驱动的流量逻辑,视频平台从注重叙事节奏的长内容转向碎片化传播的短视频形态,文学创作亦从余华、苏童等传统作家的现实书写转向男频、女频、耽美等类型文学的市场导向,而电影产业同样面临这一转型。
《消失的她》的现象级传播,恰是这种产业下沉的最新注脚。影片通过精准捕捉社会热点——从现实中持续发酵的「东南亚噶腰子」传闻到家暴议题的公共讨论,再到阶层焦虑的集体情绪——将其转化为类型化叙事。这种创作手法看似简单粗暴,实则暗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既提供即时的情绪代入,又通过悬疑结构制造认知快感。尽管与西班牙《看不见的客人》的叙事密度或《我不是药神》的社会深度存在差距,但二者的结合恰好构成了对特定观众群体的精准击中。
陈思诚的创作策略展现出独特的市场洞察力。他以马戏团杂耍般的叙事方式,包裹着看似艺术化的包装外壳。这种「廉价感与高级感」的矛盾统一,实为对目标受众的精准定位:一方面满足算法时代观众对形式感的即时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符号化表达延续类型片的传播效能。正如影片中梵高的《星空》所呈现的——唯有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符号,才能在大众认知中形成既熟悉又神秘的审美效应。这种平衡的把握,成为当代影视创作的关键命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若要寻找与陈思诚风格相近的导演,王晶或许是最佳人选,只不过陈思诚可视为更为精致的王晶版本。上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依托录像带、VCD及录像厅等载体,成为那个时代大众获取精神养分的重要途径。这类作品以市井烟火气化解了当时已显枯燥的宏大叙事,用极致娱乐消解了虚假的庄严感,为人们提供了对紧张精神生活的一次释放。其草根本质、对常规的突破、浓厚的人情味、对体制的持续警惕,以及对底层欲望的坦然展现,使观众在轻松之余获得内心的共鸣。出生于70年代末的陈思诚,显然深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正如香港电影本身存在两种对立倾向:一方面,其草根属性赋予了对普通人生活的天然关注,催生了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张之亮的《笼民》、方育民的《半边人》等作品;另一方面,当对宏大价值失去感知,又对人性缺乏信心时,欲望便成为主导,这也体现了港片的另一极。王晶的许多作品便体现了这种无节制的声色犬马,完全剥离了情感交流的可能,仿佛人生的意义仅在于满足各种欲望。相较于王晶对观众的轻视态度,陈思诚更倾向于继承这种后现代审美。在其《唐探》系列中,观众可以看到隐晦或直接的性调侃、唐仁与秦风屡次的性别扮演,以及充满暗示的男性间暧昧情节。影片贯穿始终的粉色调,与王晶作品中的表现如出一辙。这种对特定戏码的热衷与放松,源于对某种表达方式的自信,也体现了道德正当性甚至优越感。尽管这些带有30年前男性视角的性笑料在当下知识女性群体中显得不合时宜,但普通观众的积极反馈,恰恰揭示了不同群体之间认知差异的存在,以及传统审美习惯的强大惯性。

《唐人街探案2》中王宝强的表演风格颇具争议,其癫狂的演绎方式显然受到周星驰喜剧美学的深远影响。影片的动作设计亦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无论是首集警察局的混乱场面、次集纽约街头的追逐戏码,还是三集开场机场的混战场景,都可见成龙式动作喜剧的传承。在叙事结构与镜头语言上,导演团队借鉴了朴赞郁的黑色幽默、盖·里奇的非线性叙事以及诺兰的视觉实验等元素,这种跨文化的创作手法正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典型印记。
陈思诚与王晶的理念共鸣远不止表现在创作技法层面。王晶曾多次强调电影本质是商品属性,他愿意支持许鞍华拍摄文艺片《天水围的日与夜》,但坚持与艺术保持距离。而陈思诚在选角时对创作者的审美取向同样保持警惕,据说听到「阿彼查邦」这个名字会直接否定合作可能。两人均展现出对电影产业的清醒认知,认为其本质是商业运作而非艺术表达。
这种功利性创作观与他们对现实的认知高度契合。在王晶改编的《鹿鼎记》中,陈近南对韦小宝说:「这个天下就是钱与女人,底层人不明白,就要用宗教来麻痹他们。」这句台词精准折射出导演的价值取向——他更倾向于顺应大众审美需求,提供符合市场期待的娱乐产品,而非承担启蒙或教育的职责。这种创作哲学使其作品始终围绕观众喜好展开,形成独特的商业片叙事范式。

王晶与周星驰的合作中,我们并未察觉到深层情感的流露,取而代之的是表面的热闹喧嚣。尽管陈思诚主导的作品多聚焦犯罪题材,但其中呈现的并非黑暗压抑,而是借助角色死亡作为叙事展开的契机。在这些作品里,死亡往往以离奇方式发生,为主角的表演预留出充足空间,却缺乏对生命消逝的痛感呈现。人性的阴暗面被作为基调,但这种黑暗被轻巧地处理,掩盖了潜在的道德困境。创作者的表达更多源于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当这种情绪被视作理所当然时,其表达便失去了应有的重量。缺乏情感沉淀的观众难以理解真正的艺术意图,这导致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者在作品完成后难以获得预期的共鸣。例如贾樟柯对农民工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其作品难以引起目标群体的回应,因为底层民众更习惯于逃避现实,而非直面社会真相。反观都市精英阶层,因物质条件相对丰裕,拥有足够的余力关注他者命运,其情感也未在日常压力中被耗尽,反而具备释放的可能。这种创作与接受层面的错位,成为所有有道德追求的创作者共同面对的困境。观众并非完全拒绝精神食粮,而是需要在庸俗与雅致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既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种比例协调的共存。以战争片为例,其普遍具有的反战主题更多是暴力内容的包装,使得观众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血腥场面。这种包装的存在,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心理缓冲,使他们在面对自我欲望时不再感到尴尬。陈思诚在《唐探》系列中巧妙运用了这一策略,通过在剧情高潮后插入正剧元素,既为观众提供情感出口,又在过度渲染的娱乐性中注入人性深度。这种处理方式如同久经世俗纷扰的个体在深夜回归家庭,既保持了叙事的完整性,又完成了观众心理的调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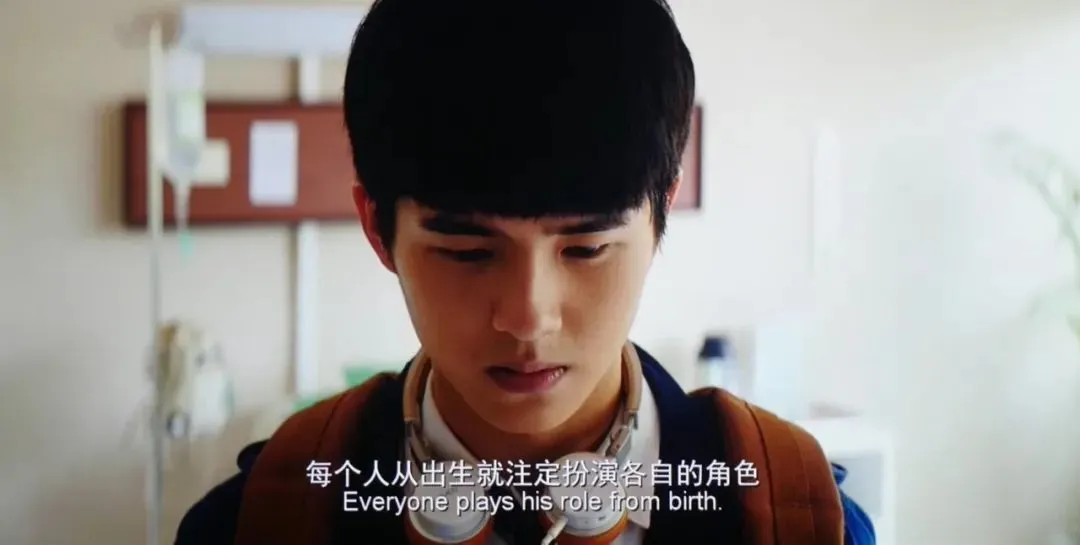
在内地电影发展的四十年历程中,《唐人街探案》系列中的秦风形象折射出电影角色功能的演变轨迹。从最初的宣传载体到后来的艺术表达,再到如今的娱乐产品,电影在时代变迁和创作者理念的影响下,其功能定位在不同作品中呈现出动态变化。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群体在转型过程中展现出鲜明的矛盾性:他们以先锋姿态突破传统叙事框架,却在时代洪流中不得不转向主旋律商业片创作,这种转变往往伴随着创作惯性的显性残留。张艺谋等导演在《狙击手》《悬崖之上》《满江红》等作品中展现出的热忱与骨子里的冷酷形成鲜明对比,其艺术探索与商业诉求的割裂感始终贯穿于创作实践。
相较之下,陈思诚展现出独特的商业逻辑。他将电影视为纯粹的产品,以产品经理的视角构建推理IP体系,在海外华人犯罪题材的创新中开辟出中国特有的亚类型市场。这种创作策略既规避了国内审查限制,又巧妙呼应着时代精神中的民族自信情绪。《唐探》系列中中国侦探横扫美日的桥段,与现实中中国民众跨国活动的场景形成互文,其刻意设计的海外地标场景更暗合了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陈思诚在创作中展现出的清醒认知,使其能够坦然面对观众需求,以计算性思维构建完整的商业链条,这种模式既区别于第五代导演的文艺探索,也超越了当前商业片创作的普遍困境。
最新资讯
- •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特辑 安雅锤哥见证史诗 -
- • 陈乔恩晒与谢娜合照 二人cos《破产姐妹》造型颜值超高 -
- • 《谈判专家》预告海报双发 刘德华演绎底层之苦 -
- • 仲野太贺与木龙麻生进出公寓 二人共度三天两夜 -
- • 《扫黑·决不放弃》上映 肖央余皑磊曝“真面目” -
- • 《最佳利益》开播获好评 天心自称戏里戏外反差大 -
- •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预告 揭秘安雅复仇之路 -
- • 2024端午档总票房破2亿 《扫黑·决不放弃》领跑! -
- • 陈羽凡被曝开豪车载女友出门 违规并线与后车发生剐蹭 -
- • 《大雄的地球交响乐》特辑 开启哆啦A梦音乐之旅 -
- • 时代峰峻就时代少年团亲属隐私权遭侵害发声明 -
- • 拒绝内耗!从跟胡歌高圆圆一起《走走停停》开始 -
- • 张婧仪进组不小心上错车 大喊“我上错车啦”超可爱 -
- • 是枝裕和新片发布感谢坂本龙一:他的配乐不可或缺 -
- • 争论不休,《美国内战》是“寓言”还是“预言”? -
- • 《扫黑·决不放弃》:这回力度不一样了 -
- • 范丞丞《奔跑吧》最新路透 cos半人马综艺感拉满 -
- • Angelababy《奔跑吧》最新路透 古装造型仙气满满 -
- • 张若昀到达襄阳进组《庆余年2》全黑look引期待 -
- • Ella陈嘉桦身穿爱心印花T恤 笑容灿烂元气满满 -